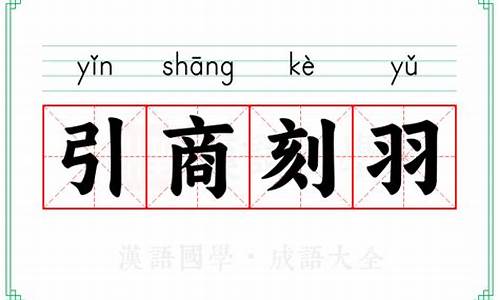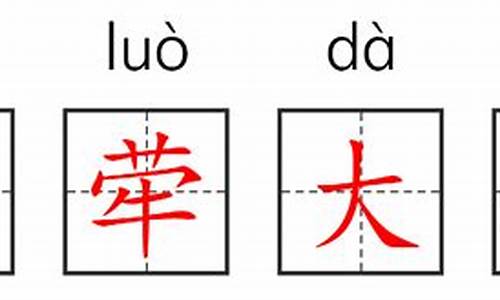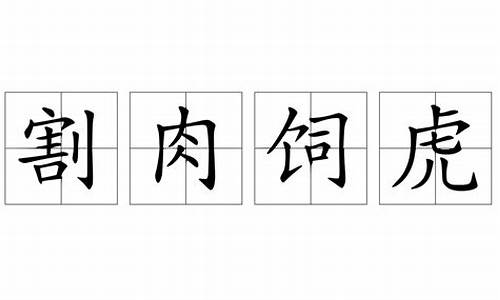石破天惊逗秋雨的逗字-石破天惊逗秋雨的逗的意思
1.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的原诗和赏析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的原诗和赏析

李贺《李凭箜篌引》赏析
李凭箜篌引 ·李贺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
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赏析一
此诗大约作于元和六年(811)至元和八年,当时,李贺在京城长安,任奉礼郎。李凭是梨园弟子,因善弹箜篌,名噪一时。“天子一日一回见,王侯将相立马迎”,身价之高,似乎远远超过盛唐时期的著名歌手李龟年。他的精湛技艺,受到诗人们的热情赞赏。李贺此篇想象丰富,设色瑰丽,艺术感染力很强。清人方扶南把它与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相提并论,推许为“摹写声音至文”(见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卷一)。
诗的起句开门见山,“吴丝蜀桐”写箜篌构造精良,借以衬托演奏者技艺的高超,写物亦即写人,收到一箭双雕的功效。“高秋”一语,除了表明时间是九月深秋,还含有“秋高气爽”的意思,与“深秋”、“暮秋”之类相比,更富含蕴。二、三两句写乐声。诗人故意避开无形无色、难以捉摸的主体(箜篌声),从客体(“空山凝云”之类)落笔,以实写虚,亦真亦幻,极富表现力。
优美悦耳的弦歌声一经传出,空旷山野上的浮云便颓然为之凝滞,仿佛在俯首谛听;善于鼓瑟的湘娥与素女,也被这乐声触动了愁怀,潸然泪下。“空山”句移情于物,把云写成具有人的听觉功能和思想感情,似乎比“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更进一层。它和下面的“江娥”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极力烘托箜篌声神奇美妙,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魅力。第四句“李凭中国弹箜篌”,用“赋”笔点出演奏者的名姓,并且交代了演奏的地点。前四句,诗人故意突破按顺序交待人物、时间、地点的一般写法,另作精心安排,先写琴,写声,然后写人,时间和地点一前一后,穿插其中。这样,突出了乐声,有着先声夺人的艺术力量。
五、六两句正面写乐声,而又各具特色。“昆山”句是以声写声,着重表现乐声的起伏多变;“芙蓉”句则是以形写声,刻意渲染乐声的优美动听。“昆山玉碎凤凰叫”,那箜篌,时而众弦齐鸣,嘈嘈杂杂,仿佛玉碎山崩,令人不遑分辨;时而又一弦独响,宛如凤凰鸣叫,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芙蓉泣露香兰笑”,构思奇特。带露的芙蓉(即荷花)是屡见不鲜的,盛开的兰花也确实给人以张口欲笑的印象。它们都是美的化身。诗人用“芙蓉泣露”摹写琴声的悲抑,而以“香兰笑”显示琴声的欢快,不仅可以耳闻,而且可以目睹。这种表现方法,真有形神兼备之妙。
从第七句起到篇终,都是写音响效果。先写近处,长安十二道城门前的冷气寒光,全被箜篌声所消融。其实,冷气寒光是无法消融的,因为李凭箜篌弹得特别好,人们陶醉在他那美妙的弦歌声中,以致连深秋时节的风寒露冷也感觉不到了。虽然用语浪漫夸张,表达的却是一种真情实感。“紫皇”是双关语,兼指天帝和当时的皇帝。诗人不用“君王”而用“紫皇”,不单是遣词造句上追求新奇,而且是一种巧妙的过渡手法,承上启下,比较自然地把诗歌的意境由人寰扩大到仙府。以下六句,诗人凭借想象的翅膀,飞向天庭,飞上神山,把读者带进更为辽阔深广、神奇瑰丽的境界。“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乐声传到天上,正在补天的女娲听得入了迷,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职守,结果石破天惊,秋雨倾泻。这种想象是何等大胆超奇,出人意料,而又感人肺腑。一个“逗”字,把音乐的强大魅力和上述奇瑰的景象紧紧联系起来了。而且,石破天惊、秋雨霶霈的景象,也可视作音乐形象的示现。
第五联,诗人又从天庭描写到神山。那美妙绝伦的乐声传入神山,教令神妪也为之感动不已;乐声感物至深,致使“老鱼跳波瘦蛟舞”。诗人用“老”和“瘦”这两个似平干枯的字眼修饰鱼龙,却有着完全相反的艺术效果,使音乐形象更加丰满。老鱼和瘦蛟本来羸弱乏力,行动艰难,现在竟然伴随着音乐的旋律腾跃起舞,这种出奇不意的形象描写,使那无形美妙的箜篌声浮雕般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了。
以上八句以形写声,摄取的多是运动着的物象,它们联翩而至,新奇瑰丽,令人目不暇接。结末两句改用静物,作进一步烘托:成天伐桂、劳累不堪的吴刚倚着桂树,久久地立在那儿,竟忘了睡眠;玉兔蹲伏一旁,任凭深夜的露水不停在洒落在身上,把毛衣浸湿,也不肯离去。这些饱含思想感情的优美形象,深深印在读者心中,就象皎洁的月亮投影于水,显得幽深渺远,逗人情思,发人联想。
这首诗的最大特点是想象奇特,形象鲜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诗人致力于把自己对于箜篌声的抽象感觉、感情与思想借助联想转化成具体的物象,使之可见可感。诗歌没有对李凭的技艺作直接的评判,也没有直接描述诗人的自我感受,有的只是对于乐声及其效果的摹绘。然而纵观全篇,又无处不寄托着诗人的情思,曲折而又明朗地表达了他对乐曲的感受和评价。这就使外在的物象和内在的情思融为一体,构成可以悦目赏心的艺术境界。 (朱世英)
赏析二
音乐是一种诉诸于听觉的时间艺术,它的音响只存在一瞬,转瞬即逝。音乐形象比较抽象,难以捉摸,要用文字将其妙处表达出来就更困难了。李贺这首诗在众多的描写音乐的唐诗中脱颖而出,获得读者的挚爱,人们将李贺这首诗与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 》并列为“摹写声音之至文”,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李贺这首诗与白居易、韩愈的诗不同。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主要通过比喻、象声等手法,力图描绘出音乐的形象。如“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大珠小珠落玉盘”;“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等就是。李贺在诗中虽然也用了“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两句来描写李凭弹箜篌的音乐形象(这两句固然写得很妙),但李贺主要不是使用描写的手法去精雕细刻音乐的形象,而是着重写“感”,写音乐给人的感受,写音乐强烈的、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
在描绘李凭箜篌弹奏的乐声给人们的感受、描绘乐声艺术效果时,诗人李贺没有按一般的思维轨迹去叙述;而驰骋自己大胆的幻想和丰富的联想,形成神奇变幻、令人应接不暇的艺术境界来表现乐声。这里试以新诗的形式,把它翻译出来。
吴丝蜀桐制成精美的箜篌,奏出的乐声飘荡在睛朗的深秋。
听到美妙的乐声,天空的白云凝聚,不再飘游;
那湘娥把点点泪珠洒满斑竹,九天上素女也牵动满腔忧愁。
这高妙的乐声从哪儿传出?那是李凭在国都把箜篌弹奏。
像昆仑美玉碰击声声清脆,像凤凰那激昂嘹亮的歌喉;
像芙蓉在露水中唏嘘饮泣,象兰花迎风开放笑语轻柔。
整个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如同沉浸在一片寒光中那样清幽。
二十三根弦丝高弹轻拨,天神的心弦也被乐声吸引。
高亢的乐声直冲云霄,把女娲炼石补天的天幕震颤。
好似天被惊震石震破,引出漫天秋雨声湫湫。
夜深沉,乐声把人们带进梦境,梦见李凭把技艺向神女传授;
湖里老鱼也奋起在波中跳跃,潭中的瘦蛟龙翩翩起舞乐悠悠 。
月宫中吴刚被乐声深深吸引,彻夜不眠在桂花树下徘徊逗留。
桂树下的兔子也伫立聆听,不顾露珠儿斜飞寒飕飕!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李贺如同一位神奇的魔术师,他驱使着大自然的静物、动物,调动了神话传说中众多的神人的形象,来写出乐声强烈感人的艺术效果,表现了李凭弹奏箜篌的高超艺术。这其中有天空中的白云、湫湫的秋雨,潭中的老鱼、瘦蛟,神话传说中的湘娥、素女,紫皇、神妪,吴刚、玉兔等等。李凭弹箜篌的乐声连没有感觉的静物、无知的动物都为之感动,连高踞仙界的神仙们也被乐声紧扣心弦。这样,抽象的、难以捉摸的乐声以及它奇妙的艺术效果,形象而具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沉浸在奇异的艺术境界之中,引起丰富的幻想。
诗人的想象是奇特的、与众不同的。例如音乐引动鱼鸟,前人也曾写过,《列子》一书说:“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 ”这种描写还是一种常规的思维轨迹。然而,李贺却是写“老鱼”写“ 瘦蛟”,这样的艺术形象就十分奇异了。又如,诗中写到“ 教神妪”,如按一般思维程式,就会说李凭的技艺高超,是神女所传授的,这样的说法就已经是夸张了,这样的描写很多,不用例举。但李贺却说李凭教善弹箜篌的神女弹奏,这就不同寻常。再如,白居易写乐声“银瓶乍破水浆迸” ,这样描写思维轨迹是一般读者能把握的;但李贺却说乐声把女娲炼五色石补天之处震破,引出一天秋雨 ,这样的写法就新颖了。此外,芙蓉哭泣、香兰笑,这样的描写也不一般。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李贺想象奇异,描绘意象新奇的艺术特色。诗人在这首诗中的幻想、联想,还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它的跳跃性。这首诗诗人的思维活动时而地下,时而天上;时而动物,时而植物;时而神人,时而天帝。他叙述的脉络没有一定的次序,而是随着诗人想象的流动,想象所至,笔之所至。这样写法,既在内容上使诗的意境内蕴丰富,变幻多样,也在形式上使诗的意境具有一种流动摇曳之美。神异的美,奇特的美,流动摇曳之美,这就是李贺这首诗具有的艺术美感。
赏析三
这是唐代诗人李贺听李凭演奏箜篌曲后所写下的感想,是一首表现音乐美的诗。箜篌(又称“坎侯”或“空侯”)是古代的一种拨弦乐器,有竖箜篌、卧箜篌等多种样式。竖箜篌可能是古代埃及和希腊竖琴的前身,东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原地区,它一般有二十三(一说二十二)根弦。李凭弹的就是二十三弦的竖箜篌。所谓“引”,原指古代一种乐曲的形式或体裁,略近于“引子”、“序曲”或“序奏”。李贺的这首诗就采取了乐府诗中“引”的这种体裁,比较自由地抒写了他对音乐的感受。
唐代弹奏箜篌的高手,最著名的就是被称为“李供奉”的宫廷乐师李凭,与李贺同时的一些诗人如杨巨源(曾写《听李凭谈箜篌二首》)、顾况(曾写《李供奉谈箜篌歌》)都曾赞美过他的高超技艺,但只有李贺这首诗写得最为出色,可以说是古典诗歌中以诗喻乐的又一绝唱!
唐诗中有不少描写音乐的杰作,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就是其中最卓绝的篇章。清人方扶南说:“白香山《江上琵琶》,韩退之《颖琴师》,李长吉《李凭箜篌》,皆摹写声音至文。韩足以惊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这评价是不错的,唯“摹写”一词有待辨析:用它来评白居易和韩愈的上述两首诗,大体上是可以的,因为他们都是对音乐形象作现实主义的描摹和比拟,例如白居易写琵琶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切切嘈嘈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低滑,幽咽流泉水下滩”。再如韩愈把琴声比做“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在表现手法上也与白居易的相类,都是用现实生活中的声音和物象来比拟乐声的。这些诗句的确是描写音乐的千古名句。
但是,用这种手法来表现音乐时,也难免其局限因为就音乐本身来说,它是一种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它不是以具体地“摹写”生活为其特长,而是以一定的声音的有规律的运动(节奏、旋律、和声、高低、快慢、强弱)来比拟(而不是“摹写”)人的情感为特征的。因此,用语言(诗或散文)对音乐加以描绘时,对其加以具体的摹写和比拟,是一种通常的办法,然而它毕竟不象浪漫主义那样可以通过更加奇特的想象和幻想式的比拟来抒发更为强烈、微妙而色层又极为丰富的心情。
李贺的这首诗主要就是以浪漫主义方法来表现音乐的。历来的注家和评论者,一般都指出了李贺在这首诗中善于活用、暗用神话典故,并着重从音乐效果上表现了一种神奇的想象,这固然不错;但似乎还没有注意到:李贺的这首诗本身就是他自己独创的一篇瑰丽的音乐神话,一幅诱人的写意诗画,一曲色彩斑烂的交响音画!阳刚阴柔的美学范畴,在这里似乎都不足以范围它的特色。这首诗创造了一种神奇美。人们只要一步入这瑰奇的交响音画的境界,就不能不在这从未领略过的神奇美面前发出惊赞!你听,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国内第一流的箜篌演奏家正在表演他的绝技,从那箜篌弦上流出的乐音,就象令人欣慰的空谷佳音,是如此的美妙动人。更奇妙的是,这乐曲的嘹亮音色,仿佛才从长安城中飞向了空山峡谷,又一下子从这山谷中飞上了高高的天空,结果竟使那飞动的秋云也凝而不流、颓然下顾,驻足聆听,这真真是“响遏行云”啊!这里的“响”,主要指音乐的魅力。你听,这奇妙的乐曲忽而又变得低沉,凄惋了,它那如泣如诉的声调,竟使原来舜的两个妃子、后来成为湘江女神的娥皇、女英也被这悲怆的乐声感动得泣啜不已!或许,这凄楚动人的旋律,本来就是“江娥”在秋夜寒空中的哀怜吧?那静绿的九嶷山,不知又要洒满她们多少深情的泪花?那早已斑斑点点的湘妃竹,因了这如泣如诉的音乐,因了这不断洒下的斑斑血泪,也将会变得更加绚丽多采吧?然而,究竟是那哀吟低诉的箜篌引起了江娥的哭声呢,还是这乐曲就象她们的悲泣,就象这两位女神滴落在斑竹上的贞洁晶莹的泪珠?或者竟是李凭在为湘娥的吟哦伴奏?……这一切,我们只有展开想象的翅膀,才能和李贺这位以想象奇特著称的诗人一起去遨游这交响音画的神奇境界!面对这美妙神奇的音乐,就连那传说中特别擅长于鼓瑟的“素女”也自叹弗如,连连发出悲愁的叹息。
《李凭箜篌引》一开篇就写出了音乐的神奇美;然而,神奇美却并不等于一味的神奇。如果艺术作品的内容与人的生活和人的感情极少联系,那么这种神奇又有谁能理解呢?李贺虽然是一位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诗人,但他的两脚仍踏在现实的土地上,并且是懂得艺术上虚实显隐的辩证关系的。以这首诗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结构层次。开头四句是一段,其中虽然交待了事由、时间和地点,但并非纯粹实写,而是有实有虚,并且重点在虚,即通过奇特的幻想写出了乐曲的动天地泣鬼神的惊人景象;接下来四句可以看作这首诗的第二个结构层次(如果以诗的感情节奏来划分,第二个大段应到“石破天惊”句为止),它侧重于实写,但仍是虚实结合。从“昆山玉碎凤凰叫”开始,分别以现实生活中的声音、物象和气氛来比喻那乐曲的美妙,即从听觉上、视觉上、嗅觉上乃至触觉上来描写和比拟那变化多端、丰富多采而又难以言状的音乐。“玉碎”用以比拟乐声的清脆悦耳;“凤凰叫”则更进一层,于清脆之外更显得清亮、高雅。人们未必都有机会听过玉碎时的音响,更不可能听到凤凰的叫声;然而,人们在大自然中和日常生活中却可能有过类似的经验。这些潜伏在我们大脑深处的听觉表象,由诗句引发而顿时活跃起来,它们似乎就是从李凭所弹奏的箜篌曲中流出的美妙旋律……。如果说,这一句主要从声音上来作摹拟,即以声喻乐,那么下一句“芙蓉泣露香兰笑”则进一步从物象上和情感上来作比拟。那曲尽其妙的箜篌声,其凄惋动人,有如一朵朵不胜寒风而呜咽悲诉的荷花,那晶莹的露珠,不正是它的声声泪滴吗?忽而,乐曲中又仿佛响起了一阵阵欢愉的笑声,这大概是秋之骄子——那高雅不凡的幽兰吧?你看,它笑得那么欣悦,那么美好,笑得张开了蓓蕾,笑得清香四溢!这些花花草草是这样多情,有如嫣然含笑的少女。在这里,香草美人既合而为一,又恍忽交错,有如**中一个个迭印的画面,又象由万花筒中幻化开来的一幅幅奇异景象,一个接着一个地从那乐曲声中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为这首交响音画增添了如此美丽的色调,把本来只能提供微弱视觉形象的音乐变得这般绚丽多姿!并且,诗人在这里不仅把听觉形象变成了视觉形象,同时又在这听觉和视觉形象中给了我们以嗅觉和温度的感触;在那神奇的音乐声中,不仅有一缕幽香溢出,更使气温也絪缊上升,以致清秋寒夜中长安城(城中有十二个城门)的“冷光”也为之消融!——“十二门前融冷光”,这句诗很好地概括了乐曲在这时所造成的热烈气氛,使我们觉得周围真仿佛洋溢着一股春天般的暖意!作者在通过语言来再现音乐的奇妙效果时很注意艺术“通感”的运用,使音响、色彩、芬芳与优美的情态融为一体,从而使人们从听觉而及于视觉、嗅觉以至于温觉和运动觉……并且使多种感觉互相交通,这样就造成了一幅五音缭绕、色彩斑烂、情态生动的交响音画,给人一种“百感交集”的特殊审美效果!
常言道,千金易得,知音难觅。刘勰就曾感慨地说过:“得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但音乐家李凭总算遇到了李贺这样的“知音”;诗人不但有一副音乐的耳朵,更有一支把音乐美转化为诗美的神笔!这的确是李凭的幸运。然而,在当时真正能够欣赏李凭绝技的人,恐怕也正象能够赏识李贺的人一样稀少吧?深受压抑的心情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这可能正是形成李贺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奇峭风格的一个重要原因。
诗的最后六句是全诗的第三个结构段。诗人在前面四句较现实的描写之后,忽然又随着那美妙的乐曲,让自己的想象飞向了更加神奇的境界,那奇妙的音乐这时竟穿过天空中的凝聚的乌云,直上九霄,致使女娲娘娘当年采用五色石补过的那块天壁也为之震撼破裂,终于“石破天惊”,秋雨大作了!这音乐的伟力是何等的强大啊!把音乐的感染力描写到这样神奇,达到了这样“异想天开”的地步,真可以说是“笔补造化天无功”了!在这样奇特的想象面前,我们能不发出由衷的惊赞么?诗写到这里,似乎已经登峰造极,难以为继了,谁知诗人的笔锋陡然一转,又把我们从九天之上引入深山大泽之中,“梦入神山教神妪”——使我们仿佛看到了李凭正在云雾缥缈的海上仙山中向神仙传授他的绝技,那位传说中最善于弹箜篌的年老的女神成夫人也不得不为李凭的绝技所倾倒,竟情不自禁地合着乐曲的节拍跳起舞来;甚至连江河海湖中的鱼龙听了这美妙的音乐也乐不可支,以致它们当中的那些“老鱼瘦蛟”都不顾自己的年迈体弱,也随着这优美的乐曲在水波中翩翩起舞了!这是何等奇特的景象啊!或许,这本来就是从李凭那支单纯的弦乐器中幻化出来的一幅水光波影,龙腾鱼跃的图画吧?或许,这一切也并非纯粹的神话和幻想;现代科学不是已经证实了吗?优美和谐的轻音乐不但有益人的身心,而且真的可以使母鸡多下蛋,西红柿多结果,连那俏皮的海豚,有时也会在音乐声中不停地跳跃嬉戏……然而,正当我们神往于这美丽的遐想,这音乐与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无穷奥妙,想要在这里流连一下之时,诗人突然又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更加想象不到的世界。这神妙无穷、无远弗届的音乐,忽然又从深山大泽中一跃而起,直上兰天,带着我们一起飞向了那皎洁如琼楼玉宇般的月宫神殿,让我们看到了在月中伐桂的吴刚(即“吴质”),居然也被这奇异的音乐弄得如醉如痴了!——在“吴质不眠依桂树”这个罕见的奇句中,诗人那非凡的想象真是愈飞愈高,愈高愈险,愈险愈奇!你看,这神奇的音乐竟使吴刚也中断了他那永不休止的劳作,甘冒遭受天廷的严厉惩罚,索兴扔下了手中的斧头,靠在那棵巨大的桂树上出神地欣赏起来了!这时夜色已经深沉,寒雾从月空降下,那萧瑟的金风又把这寒雾斜吹进树荫之中,淋湿了吴刚的衣襟,淋湿了干燥的月面,整个月宫都披上了一层轻纱似的薄雾……然而,这位神仙中的苦役犯在这时早已忘掉了周围世界的一切,忘掉了疲劳,忘掉了睡眠,也忘掉了天界对他的不公正的待遇,完全浸沉到李凭那美妙神奇的乐曲声中去了……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活用典故而又自铸伟辞。李贺在这首诗中用典时不仅十分灵活,而且更把它们几乎不见痕迹地熔铸在自己独造的奇峭词句和形象之中。本来,我国古代有很多关于音乐的神话传说,诸如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或师旷鼓琴“大雨随之”等等,但这些神话传说都显得比较原始而简略,主要是从效果上来夸张音乐的神奇,往往缺少生动具体的形象;李贺则根据众多的神话传说进行了综合加工,匠心独运地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
这首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虚实结合的手法的运用。诗人以这种手法,把我们引入了一个类似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艺术幻觉”的真实之中,其实这也跟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中十分重视的艺术形象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道理有相通之处,正是在这种浪漫主义的“离形得似”的艺术境界中,我们获得了一种类似康德所说的想象力与理解力得以和谐合作与自由运动的快感。你看,诗人写李凭弹奏的乐曲,不论是“江娥啼竹素女愁”,也不论是凤凰叫,香兰笑,融冷光,动紫皇,舞鱼龙,逗秋雨,吴质不眠等等,这些情景,意象,如前所说,无不具有双重的或多重的含义,并不只是单纯从效果上来表现音乐。清人王琦就因为不太懂得这种“似景似情,似虚似实”、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的艺术辩证法的奥妙,把这首诗的几乎每句都当成了“显然明白之辞”,他自然就难以把握这首浪漫主义音乐诗的美学特征了。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